《古代法》读书报告
一部经典著作不同于平庸作品之处,就在于对原初的问题以新颖的论述作出了强调。正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导言里说的:“旧有的真理若要保有对人之心智的支配,就必须根据当下的语言和概念予以重述。人们在过去对旧真理所做的最为有效的表述、已日渐失用,因而也就不再含有明确的意义。”特蕾西在《诠释学、宗教、希望》中也提到,“站在更为明确的诠释学立场上,经典是那些负荷着过剩的和持久的意义,然而却总是拒绝定论性解释的部分。”换言之,一部作品是否成为经典,要看它主题恒久的价值和本身可承受解释的张力。
梅因的《古代法》正是如此。 从历史背景上看,梅因促使人们对形成法律的各种力量加以重视,而不是只服从于先验的自然法图式。十九世纪流行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被人们看成唯一的理解法律的路径,梅因指出了这种思潮的偏颇和浅薄。 对于奥斯丁为代表的分析法学派,梅因的观点是“主权者的命令”一说至少在法律产生时并不符合事实,并且它可以解释的问题也有限,尤其是对于“宏大叙事”型的法律发生发展解释缺乏力度。与他们坚持只研究实际执行的法律不同,研究法律历史的梅因仍然希望对“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作出回答。 梅因在研究中提出的问题是,法律在过去的年代里究竟是如何发展的,研究的目的是解决法律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垦扑在导言中提出的梅因对于自然法的批判,实际上是“历史方法”产生的必然结果:既然过去是如此,我们据以作出判断的经验又只来自过去,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现在和将来的法律不是如此呢?在我看来,这是《古代法》成书的前提。 然而,梅因的不足恰恰蕴含在他的伟大之中。 无论梅因、奥斯丁还是卢梭,实际上都是法律的解释者。奥斯丁的基点是普通人对法律的态度,卢梭立足于“为什么法律应当遵守”的冥想,而梅因则通过对法律本身发展史的描述阐述他的法律思想。奥斯丁为代表的分析法学派并没有把学说扩展到法律的起源,卢梭学说(在后来的发展中)也不以实际存在的自然状态为前提。两者实际上都小心的限制了自己解释的范围。而梅因在古代法中却试图作出一个根本性的解释:历史是如此,现在即如此,将来也必如此。 这样,梅因的法律思想的全部立足点就放在了他所考察和解释的“历史”上。梅因强力批驳了对罗马法上的万民法的错误见解,得出“从身份到契约”、“判决-习惯-习惯法-成文法”等一般规律,可谓字字珠玑。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历史果真如此吗?梅因自己不是评判的标准,我们也不是,谁是? 梅因的开创的历史法学派被后人称为“立基于历史和传统的保守思想,开始为人们所强调并广为宣传。在法律和法哲学领域,这意味着对法律的历史和传统的强调,进而反对从思辩的角度建立自然法的企图。法律和历史得到了彻底的研究,而法律改革者的热情则得到了阻碍”。 解释者本身被解释,不知梅因本人看了会如何回应。梅因揭示了当时鲜为人知的许多事实,可是:首先,历史资料是有限的,现存的资料是否足够对一时代的法律加以研究并归结成一种简单的图式,可以存疑;其次,以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眼光,绝对不可能反映历史全景。如福柯等被贴上“后现代”标签的大师对历史本身的反思得出了颠覆历史的结论,我虽不认同那么极端的观点,但至少可以肯定,梅因也只是历史的解释者,而不是历史本身。 梅因提出了法律发展的一般图式,其基础是《古代法》不只一次的提到的人类社会的幼年、成熟期。对理解《古代法》有帮助的是,梅因作为法学家的同时,还是一个作为一个“文化进化论”者的人类学家。认为社会发展是单向线性的,是早期人类学理论的共同特征。马林诺夫斯基曾对文化进化论作出了如下评价:“……和进化主义相结合的比较方法,包含着若干一般性的假定。人类实质上都是相互类似的。人类从原始状态向前发展,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进化阶段。根据对大量资料的比较、归纳,可以发现人们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和思想过程中的公约数。……残存理论……随着对各发展阶段的追溯,可以发现我们所能够知
道的最原始的阶段,即种种制度以及概念和习惯的起源。”后来的人类学已经在一般的意义上摒弃了这些早期的偏见, 如功能派人类学对进化论的批判是“任何具体的社会文化都是有机、自动、自足的功能整体,整体之内的任何部件,都要挂靠在其对整体的功能上才能认识。整体是跨文化比较的合法单位。拆卸整体中的功能部件去拼装进化或传播的抽象图式,在实践上是伤天害理,在认识上是自欺欺人。” “进化论”的历史方法蕴藏的风险不仅是理论上的偏见和独断,它和历史决定论的关系也显而易见。现代已经有一些哲学家对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作出了反思,结论是意识形态统治的历史悲剧并不仅仅来源于东方专制传统,而是内在于决定论本身。 实际上,关于历史的“进步”,《古代法》中的一些观点也呈现出很大的张力。梅因对于历史的判断决不是离开了自然法——梅因的研究让人感觉出某些“历史的规律”,但由于历史并不能说明法律应当成为社会秩序的理由,自然法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样,梅因仍然没有成为一个叛经离道者。梅因也提到“如果自然法没有成为古代世界中的一种普遍信念,这就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了。” 这正是进化论作为社会文化理论的致命之处;进化论不应当受到信念、理想这些上层建筑(借用马克思的术语)的决定,否则就难以自足,难以否弃超验的观念达到纯粹。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梅因的理论,我们就不会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所谓〈古代法〉真正的复兴了历史研究方法并反驳了自然法,并不在于梅因发现了历史研究的唯一正确的途径,而是促使人们重视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法律,从而打开了“显现” 的另一路径。而这,正是经典的特征。
第二篇:古代法1
220330671.doc
小引
亨利·梅因(Sir Henry Maine,1822—1888),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法律史学家,著有“古代法”、“古代法制史”、“古代法律与习惯”和“国际法”等书。本书发表于1861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梅因在本书中收集了有关古代法的若干材料,它对我们研究古代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他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和推断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主义的艰点出诊的,因此在阅读本书、特别是利用书中材料的时候,应当持分析的态度,不要被它的花花絮絮的资料和似是而非的议论所迷惑。商务印书馆将本书重译出版,作为学术批判材料,这是很必要的。
梅因在他的著作中有这样的错误论调:一个国家文化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大凡半开化的国家,民法少而刑法多,进化的国家,民法多而刑法少。他这几句话被资产阶级学者奉为至理名言,日本有的资产阶级法学家更据此对我国大肆诬蔑,说中国古代只有刑法而没有民法,是一个半开化的、文化低落的国家。就在我国,也有一些资产阶级法学家象鹦鹉学舌一样,把自己的祖先辱骂一顿。事实上,古代法律大抵都是诸法合体,并没有什么民法、刑法的分别,中国古代是这样,外国古代也是这样。国家的先进和落后要具体地历史地来考察,主要要从其社会制度是否适合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来衡量,而不能单以作为国家上层建筑之一的法律制度之完善与否为尺度,至于民法与刑法的比例则更不是一种什么准则。因为梅因的这个错误论调曾经迷惑过一些人,因此特为指出。
李祖萨
19xx年2月
序
本书的主要目的,在扼要地说明反映于“古代法”中的人类最早的某些观念,并指出这些观念同现代思想的关系。如果没有像罗马法那样的一套法律,本文中企图进行的研究,多数将不能有丝毫希望达到有用的结果。因为在罗马法的最古部分中,有着最久远的古代事物的痕迹,而在其后期规定中,又提供了甚至到现在还支配着现代社会的民事制度资料。由于必须把罗马法当作一个典型的制度,这使著者不得不从其中采取了数目似不相称的例证;但他的本意并非在写一篇关于罗马法律学的论文,他并且尽可能竭力避免足以使其作品具有这样的外貌的一切论述。第三和第四章以一定篇幅用来说明罗马法学专家的某些哲学理论,这样做,有两个理由。第一,著者认为这些理论对世界的思想和行为,比一般所设想
Franc.She 1
220330671.doc
的有较为广泛、永久的影响。其次,这些理论被深信为是有关本书所讨论的各个问题直到最近还流行着的大多数见解的根源。对于这些纯理论的渊源、意义与价值,著者如不说明其意见,则其所承担的工作,将不能做得深入透澈。
亨利·梅因
导言
有关法律的书籍,不论是古代法或现代法,并不常常能吸引很多的读者;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分别产生了一本著名的法律书籍,对当代的和以后的思想发展方向,有着深远的影响。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论法的精神”(L’Esprit des Lois)是法国十八世纪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标志着历史法律学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虽然具有梅因在“古代法”(第五章)中所评论的某些偏颇之处。“古代法”在十九世纪执行了甚至更为重大的职能;真的,就英国而论,如果说现代历史法律学是随着这本书的出现而出生的,也不能谓言之过甚。
虽然在梅因的卓越的文体中所表达的,有一些也不能认为是普通的东西,但“古代法”中有相当部分,在过去七十年中,几乎是学习法律制度的学生所不可或缺的。为了要能体现它在当时是怎样一个独具见解的作品,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当时流行着的一些智力状态。
1758年时作为第一个佛尼林派教授(Vinerian Professor)的布拉克斯顿
(Blackstone)进行了未有先例的试验,他在牛津大学讲授英国法律。当时,他不得不用法律研究是一个有教养绅士的一种适宜的职业来说服他的听众;虽然甚至他自己或许也不会相信这是像猎狐一样一种非常绅士般的职业。七十年以后,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在伦敦大学以法律学的吸引力与实利向其听众吹嘘(结果收效很少),同时却坦白地承认有许多心地宽厚的人们不愿研习法律,主要是由于它所来自的渊源,其性质“令人可厌”。有一次,他这样写道,“我胆敢断言,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没有一套法律会像我们的那样缺乏一致性和均称性”。除了海尔(Hale)和布拉克斯顿外,没有人曾把它作过有系统的阐明。过去,法律是根据有试验必有错误的原则学习的,现在还活着的一些老法学家可以记得那样一个时期,用一个著名的美国老法官——荷姆斯法官先生(Mr.Justice Holmes)——的话来描写,法律只是一麻袋的琐细东西;真的,在某些开业律师中,赞成用这种纯粹实验的、听天由命的方法来精通法律的偏见,甚至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除。
至于英国的法律史,不仅被忽视了,简直是被蔑视了。例如,边沁(Bentham)竟然建议——除了作为批判之外——完全不顾所有的先例而把英国法律全部重新写过:对于他,甚至其最卓越的学生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不得不说,“他宁愿完全不顾过去的全部成就,而重新从头写起”。如果对于英国法2 Franc.She
220330671.doc
律史的态度是这样,那就可以想象到,对于外国制度或对于今昔法律现象的比较研究,又将会有怎样轻蔑的感情了。
这种褊狭的心情,在对待罗马法上,特别显而易见。1816年尼布尔(Niebubr)在维罗纳(Verona)发掘到该雅士(Gaius)“法学教典”(Institutes)的手稿——这当然是学术史上最著名的发现之一:因为这篇论文不仅是我们对于古代罗马法律甚至是我们对于雅利安(Aryan)法律一些最有启发性的方面的唯一知识来源,并且在它写成四百年后的一部不朽杰作查斯丁尼安(Justinian)的“法学阶梯”(Institutes)曾根据其中极大部分作为编纂的范本。英国对这样的重大事件漠不关心。在本书第九章中,可以看到梅因痛切地——最终是有效地——抗议“对罗马法的无知,这是英国人欣然承认,且有时不以为耻地引以自夸的”。
但是,对于过去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中可以确定的事实,不愿加以探究的情况,不独英国如此。全欧洲有许多关于政治社会、自然法以及“自然状态”的起源的假说,这些假设从现代观点看来,似乎是很可笑,并且一点也不像历史上的事实,以致在今日,我们竟难于理解他们怎样会这样强有力地深入当时人们的想像的。我们必须耐心地、宽容地、并且也许谦逊地(否则将来我们自己的信念也将同样地成为毫无根据)牢记着梅因所说的“推理的错误的非常活力”。这使我们记起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意见,即“一种思想体系在自杀以后,有可能精神焕发地到处流行”。十八世纪中流行着的关于政治起源的各种观念,在卢梭(Rousseau)的奇怪的假定中达到了极点,并且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即使已濒于死亡,却仍活着、呼吸着,但如果说这些观念在过去二千年的长时期中实在一无进步,那是不能说是言之过甚的。关于社会人的性质,同这些虚说讽喻同时流行的,另外有一种广泛传布的信念,认为政治历史是一些退化的而不是发展的故事,认为人类及其大部分的制度已从一个神秘地遥远的时代的较为幸福的状况中趋向衰颓。因此,既然恢复原始的天真状态已不可能,则我们为民族所能做的最好的工作就是珍惜地保存事物的现存秩序,至少要阻止它进一步堕落。
由于对历史的藐视,幸而它是同比较体面的动机相结合着的——一种动机是对于这种卓越的自然法的正当反应,另一种动机是要对法律概念的实质进行有系统分析的一种非常及时的愿望——,就在英国产生了另一种法律理论,这主要同霍布斯(Hobbes)和奥斯丁有关,但和边沁也不无关系。这种理论,我们为了便利称它为法律与主权的命令说。它认为法律最突出的是一个在法律上有无限权力的主权者或“政治领袖”对一个臣民或“政治下属”所颁发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后者既被假定为具有服从的习惯,就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对于自然法或理想法中模糊的赏罚观念发生着怀疑,并且是正当地怀疑,它就集中其全部注意力于现实法的强制性质,至于它在历史上或伦理上的各种要素,则坚决不加考虑。这种理论
Franc.She 3
220330671.doc
虽然在其他地方很少受到注意,但在英国直到现在仍旧常常被讨论到;不过至少有一种意见是大家一致同意的,即它既然从法律学的领域中排斥了历史的考虑,就使它陷入了一种根本的谬误,即把一切法律制度都认为是以西欧的君主国家作为典型的。
对于这些倾向,不是没有阻力的,这些阻力就存在于梅因的作品中。德国有一个丰·萨维尼(Von Savigny),他是历来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他在十九世纪初期曾对十八世纪非历史的思想习惯加以激烈的攻击。虽然他对于国家法律与习惯并没有真正找到一种科学的历史的研究方法,但他提供了向这个方向努力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从事于法律学研究的精神,辉煌地表达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此种精神在以后就从来没有被人们舍弃过,虽然其中有些夸张之处,随着时间的变迁已有所变更。他在英国很少直接影响,就是曾在德国求学的奥斯丁,也常常反对他所提出的结论,并且我认为虽然没有很多证据,足以证明梅因非常熟悉丰·萨维尼及其门徒的著作,但他是深知他们的观点的一般要旨的,并且无疑地在实质上是同意这种观点的。梅因可能从洛多尔夫·丰·伊叶林(Rodofe von Ihering)在1858年出版的巨著“罗马法精神”(Geist des Romischon Rechts)受到更加直接的影响。伊叶林在几个重要问题方面,与萨维尼的观点不同,但他肯定地主张把历史方法用于法律学中。他也对罗马法的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和活泼的精神,与长期在德国压制着罗马法的无生气的经院哲学派不同;有许多证据足以表明这对于梅因是一种真正的刺激,正像吉朋(Gibbon)对伊叶林同样是一种刺激一样。
“古代法”出现的时期,也是人类思想史上有最深远影响的事件之一,即达尔文(Darwin)自然选择原则形成的时期。
“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发表于“古代法”出版前两年。在梅因的主要著作中,据我所知,只有一处直接提到了达尔文;在“古代法律与习惯”(Early Law and Custom)第七章中,他认为达尔文从自然科学上提供了有利于父权制理论的证据。究竟梅因是否接受进化论的理论包括其全部含意在内,这是本文作者所不了解的,但梅因在历史法律学方面的著作自然地同十九世纪中叶广为传布的新的研究精神平列在一起,则是没有疑问的。
关于这种“新学问”,就其对法律的影响而论,梅因的全部著作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有生气的表现。他对那些不科学的、缺乏批判的,被野蛮地但简略地称为“先天主义”的那种很盛行的思想习惯,从不放松加以反对。他在“古代法制史”(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es)(第十二讲)中写道,“为英国法学家一般接受的各种历史理论,不但对于法律的研究有很大的损害,即使对历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因此,当前英国学术上最迫切需要增益的,也许是新材料的审查,旧材料的再度审查,并在这基础上把我们法律制度的来源及其发展,加以阐明。”对英国法律应该4 Franc.She
220330671.doc
这样,对其他一般法律也同样应该这样。在“古代法”中,梅因对当时流行的政治纯理论中最为旁若无人的、根深蒂固的某种“先天主义”给以第一次的攻击(这在他以后的著作中,常被重复地进行着)。例如,在第四章中的“‘自然平等’的教条”,第五章中的“幻想的‘自然状态’”,第八章中的“认为财产起源于单独的个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这毫无根据的观点”,第九章中的“社会契约的梦呓”,没有一个人曾像他那样恶毒地辱骂这些一度声势极盛的说教的严重错误。他说:这些有关“世界最古年代人类情况的描写受到这两种假设的影响,首先是假定人类并不具有今天围绕着他们的大部分环境,其次,是假定在这样想像的条件下他们会保存现在刺激他们进行活动的同样的情绪和偏见”。至少对于英国,梅因可以说是已经改变了“自然”的面貌。
这种智力状态使梅因完全不可能接受霍布斯与奥斯丁的主权命令说,把它视为是一切法律的起源和性质的特征。这是在“古代法”最初的篇幅中就加以说明的;并且他在十四年后出版的“古代法制史”最后两讲中更深入地加以发挥。奇怪的是,梅因虽然是奥斯丁最严格的批评者之一,但他把奥斯丁在法律分析上所作努力的真正成绩推荐给英国法学家,则有甚于任何人。奥斯丁在1828年所作的演讲,除了培养人才补足审判席缺额以外,似乎很少成就;他的演讲集在1832年出版时,依旧毫无影响;只是通过了梅因的各种著作和他在1852年对法学院所作的演讲才把这一热诚的、太过热诚的真理追求者所作耐性的但落空的努力,从湮没中援救出来。但是,虽然他对奥斯丁的分析天才比以后许多争论者给予更多的赞誉,但他对于把法律视作为命令,并且只是命令这一个论点,却无疑地论证了它的缺点。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梅因对于英国人对罗马法的“极端无知”,提出了非难。1847年,他接受了剑桥大学民法学钦定讲座的教授职位,因为这个任命,使他得以专心研究古代法而获益不少。在关于罗马遗嘱(第六章)、法律诉讼(第十章)、家父权(第五章)以及罗马契约分类(第八章)等这些辉煌的纲要中,包含着许多新奇的东西,这些东西现在虽已毫不新奇,但在1861年它们都是很新奇的;我们必须指出其中也有许多到现在已成为有疑问的了,但是,对于并不熟悉专门的罗马法的读者,还不能在英文中找到一本书,能对那伟大法制中某些独特的制度,“像古代法”这样提供生气勃勃的说明,并且就罗马法对于欧洲人生活上和思想上几乎每一个部门所发生的巨大影响,现在当然还找不到比第九章中所作的更好的、更有说服力的描写。还不很熟悉这一切的读者,可以从吉朋所著“罗马帝国衰亡史”这一无比精辟的书的第四十四章中找到很适宜的补充材料。
梅因与进化论学派的密切关系,可以从他对于法律制度史中某种进步因素所具有的确实而决不空洞的信念,明白表现出来,他完全意识到进步一字的含义含
Franc.She 5
220330671.doc
糊:在其无数警句之一中,他告诉我们:“对于人们,不论是个人或是集体,没有东西比把他们的道德进步认作一个实体的现实性,更可厌恶的了”;他认为绝大部分人类往往对于任何有意识地努力改进民主制度表示漠不关心,对于这种现象,他表示大为惊奇(见第二章)。他从不怀疑,社会是明显地向着一种稳健的坚实的方向前进的;这样,在契约的发展史中,他发现了善意这个道德观念的逐步出现,并且虽然从没有停止和自然法非历史性的谬论作斗争,但他依然在其中看到了一个可以促使改进的有力因素,以反对法律的保守主义的禀性,即认为法律是只能通过相当难以运用的如拟制、衡平和立法等权宜手段来改进本身的。他同样清楚地认识到社会是天然地分为“进步的”和“不进步的”的——这种两分法,相当于西方与东方的两分法。他不愿为“进步”的标准下一个定义;但在“古代法制史”中,他提出了至少两种可能的区别标准——一种是有意识地采用对最大多数人给以最大幸福的原则作为立法政策,另一种是对待妇女地位的流行态度。有许多其他标准可以提出来讨论;没有一个可以不变地加以应用;但谁会怀疑,在进步的社会和不进步的社会之间确有不同,或是谁会认为,梅因在这样相信了以后已作出了过分满足的假设呢?
在进一步介绍“古代法”中某几个时常引起争论的部分以前,必须首先注意到本书的一个独特之点。大多数人在对某一门科学作专门研究时,在发表(如果他们的确发表了)他们的一般结论前,必先就其各个细节,加以详细研究,并可能要先加以说明。而梅因的做法,恰恰与此相反。在其第一本书中,他叙述了最粗糙的一般原理,而在他所有的后期作品中,除了二本比较不重要的之外,只是用了更详细的和更明确具体的例证,以深入阐明他在开始其专业时新提出的各项原理。这种方法是大胆的,并不是毫无危险的:除了对于事物的要点具有非常的直觉的理解力的人,采用这种做法,很难获得成功。学者们为了使其结论能达到精确无误,一般对于概括是非常谨慎的,有时简直是不健康地谨慎;但是对于“古代法”,如果真有任何成语与它联用得最最经常,那就是“辉煌的概括”这一个成语。在“古代法”中,很少有一页没有几句著名的警句,突出于字里、行间;可怪的是,梅因在经过长期的辛勤的进一步研究后,竟发现很少有必要就其最早的意见,进行修正。这本书充满了渊博的知识,却没有表示博学的一般附属物;究竟是由于政策,或是由于厌恶,还是由于无能,无论如何,梅因坚决拒绝采用似乎常常需要的旁注和详细证据,以为其明白直率的主文的累赘。虽然其结果有时使经过专门训练的读者感到不便,但免除学术上的累赘,无疑地大大增加了“古代法”和梅因的其他一切著作的声望。我们享受着文字的乳汁,而不被迫目击挤乳的这种繁重的、有时候很辛苦的劳动,虽然在“东西方村落共产体”(Village 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1871年)、“古代法制史”(1875年)及“古代法律与习惯”(18836 Franc.She
220330671.doc
年)中都用了比“古代法”更正确的、更有批评眼光的考查以观察古代法律中的各个问题,但梅因在“古代法”之后写的一些作品,都不及这个初生儿,甚至一半也及不到。
因此,“古代法”应该被认为好像是梅因毕生工作中的一个宣言书,这是雅利安民族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的一个比较研究。由于它本身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统一体,它不能被视为仅仅是一篇绪论;不过,对于他粗糙地谈到的许多问题,如果要获得更丰富的知识,读者还必须借助于梅因的后期作品。例如第八章提到的村落共产体是一篇用同名的完整的(虽然是简短的)论文的主题,由于当时那士(Nasse)和G.L.丰毛勒(G..L.von Maurer)的新近研究而引起的;关于父权家族的说明,当然应该以“古代法律与习惯”为补充材料,这是梅因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在其中,他用了同样的说服力和机智,乘便对主张母权制理论的几个主要代表人予以答复。在这里,由于篇幅的限制,难以就“古代法”中讨论的各个题目,一一指出究竟在他后期作品中哪些地方曾详加说明;但就主要的题目中,可以提出的有主权、集体财产的早期形式(其重要的一方面,即联合家族,在“古代法”中没有提到,但在“村落共产体”和“古代法制史”中,都有详尽的讨论),封建制度化的过程,各种古代法典(例如在“古代法律与习惯”的第一章中,详细叙述了“摩奴法典”),法学家[特别是罗马法学专家(Jurisprudentes)和爱尔兰“古代法官”]在制成法律上所起的影响,原始的亲属关系,动产所有权(关于第八章中所讨论的要式交易物(resmana cipi)更详细的说明,可参考“古代法律与习惯”第十章),土地所有权,长子继承权,拟制(例如,关于收养这个拟制的补充说明,可见“古代法制史”第八讲和“古代法律与习惯”第四章),原始诉讼程序(著名“戏剧化”的誓金(Sacramena tum)可在“古代法制史”第九讲中再发现),强制执行的各种早期形式,祖先崇拜和家族圣物,以及衡平的发展等。
“古代法”中有许多部分,在后来成为批评或者有时是别人所不同意的主题,对于这些,只可浏览一过。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梅因的名字也许最容易同父权制的理论联系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以巴觉芬(Bachofen)(他的“母权制论”(Das Mutterrechet)由于巧合,恰在“古代法”出版的同一年中出版)、马克林南(Mclennan)、摩尔根(Morgan)、约瑟夫·库勒(Josef Kohler)和法拉善(Frazer)为其主要代表人物的反对学派,主张人类社会以一个人群开始,其中男女两性处于一种没有节制的杂交状态中互相匹配,主张首先出现的家族集团是以母氏为中心的,并且主张以认定的生父的体力和独占禁忌占优势的家族集团,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属于一个较后的阶段。而在“古代法”和“古代法律与习惯”的简要研究中,显然梅因所描写的
Franc.She 7
220330671.doc
社会,既不是一个以“自然状态中的人”也不是以母系子嗣,而是一个以父权的、宗亲的家作为单位的社会。
但是,梅因所重新假设的这种共产体,从来没有要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渊源的代表之意。他的研究明白地限于雅利安民族,尤其是其中比较进步的几个支系(但有显著的例外,如印度村落共产体);虽然在其他方面可能有些争执,但雅利安家族制度主要是父权的,这是没有争议的。在“古代法律与习惯”中,梅因不但不主张人类种族的各个支系应该有一个单一的、一成不变的发展图式,他并且毫无隐瞒地对这种想法表示着怀疑。现代学说所主张的,正和这个意见相同:现在认为,把父权制理论和母权制理论作为相互之间不能调和的对立物是完全人为的。男性和女性在家族中和社会上的相对重要性决定于许多变化着的情况,譬如各家族集团是孤立的还是互相邻接的,男女两性的相对人数,战争的影响,可用以瞻养妻子的财富,灭婴的习俗,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因素,决不可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点,完全相同。即使在大量证据中仅仅熟悉其中一部分的人(或仅仅熟悉其中可靠部分的人,并且不包括梅因讽刺地称之为“道听途说”的人),现在也不再怀疑母系的安排曾流行于世界的许多地方。梅因曾被责难为在承认马克林南和摩尔根所提出母权制的证据时过分勉强,并且过分严格地坚持着男性的体力和性的忌妒这些支配的因素。实际上,梅因完全承认父权制并不能适用于一切形式的社会;他所主张的,只是父权制是雅利安人所特有的,同时母权制的证据并不足以支持有一种原始群杂交的通说而已。对于这两种说法,现代的意见都支持着他;任何普遍的原始杂交的假设,现在为一般人所不信,虽然作为偶然的热情奔放的那种所谓性的共产主义,证据还是不少;在雅利安人中间确有母权制的遗迹,但他们认为这很可能不是人类家族中这一支系的一种较古时期的原有情况,而是它同非雅利安种族习惯相接触的结果。
梅因的行文流畅,偶尔(但只是偶尔)也有自相矛盾之处,这是不能毫无保留地加以接受的。这类矛盾在“古代法”最初的篇幅中就可以看到,在第一章中,关于半司法的、半宗教的θCμιDC觉得出了在原始社会中“判决先于习惯”的结论。在“村落共产体”中,梅因回到了“主权者有权创造习惯”。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信念的学派;一派主张在最古时期高级官吏的宣告只是宣布业已存在的习惯,另一派则认为这些宣告却真正是创设和塑造通俗惯例的决定因素。
真相似乎是在这两种相反的观点的中间。毫无疑问,早期的判决,不论是国王的或是祭司的,不论是纯粹世俗的或是幻想为神灵所启示的,在确定习惯的形式、范围以及方向上,确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一切证据似乎都说明,最古时期的司法职能被认为是以发现现存的法律为其主要目的。在西方世界,到处都有关于这种“发现法律”以及以发现法律为专职的公认专家的各种记录。甚至在解释8 Franc.She
220330671.doc
过程中采用了(这也常是必然的)新的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已从单纯的宣布进入了创设的时期,甚至在这种时候,这种改革仍旧被装扮成只是发现:正像英国法官在实质上是把新的成分转入到法律中去,却仍旧尽可能地把它们说成是根据于现存的先例一样。梅因对于这种看法,曾经详细考虑而加以同意,因为在“古代法律与习惯”(第六章)中,当他写到θCμ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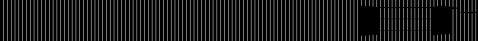
DC
自早已存在的习惯或惯例”;虽然他也许是为了表示公正起见,接着说:“这观念是,它们是由国王自发地或经过神的提示而想出来的”。
“古代法”中没有一部分像万民法(ius gentium)的叙述那样需要更多的详细说明。“古代法”的最大缺点,在于它跳过了从罗马人到格罗秋(Grotius)之间的几个世纪,忽略了中古世纪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自然法”转变成为有无限活力和影响的一种神学概念。对于像梅因这样有非常的均衡感和透视力的人,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遗漏,而每一个读者希望对这一漫长时期的法律理论有比较正确的印象的,应该至少参考一下布赖斯爵士(Lord Bryce)和菲莱特烈克·濮洛克爵士(Sir Frederick Pollock)关于“自然法律史”的几篇论文,以及A.J.喀莱尔博士(Dr.A. J.Carlyle)的“西方中世纪政治理论”(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West)。
梅因对于罗马契约法发展的说明,是他论文中最雄辩的部分之一。但这部分有些浪漫的倾向,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在有些方面,他似乎显然是错误的;例如约定(stipulaio),根据现代意见,不能被真正地认为是来源于耐克逊(nexum):它也许在宗教的神圣性中有完全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来源。在其他方面,如关于耐克逊的确切性质,他所表示的见解,有些也只能认为是似乎可信的猜测;但这样说,并不能被认为是对他责难,因为从梅因的时代起,对于这一个问题曾发生过无休无止的争论,而争论的结果也还只是一些可能和推测而已,实际上,以证据而论,也只能得到这样的结果。梅因对于罗马契约的历史分类存在着真正的弱点,这与罗马法学家自己对于合意的分类的存在着弱点,完全相同——弱点是在于它图表式的但靠不住的单纯。梅因所提出的各个阶段是:把债务同真正的以身体自由为质物(耐克逊借贷)看做一回事,带有严格的神圣仪式;其次是以庄严的口头问答和以诚意担保的债务;其次是有书面文字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其次是真正契约的“巨大道德进步”,这些契约代表着公正的基本原理,即根据一致同意的条件,受领和享有他人有价物件的人,有归还它或其价值的义务;其次是在任何经济发达的社会中,在四种最普通和重要的交易中一致的效力;以及最后,通过裁判官(pretor)的自由学说,在任何严肃的和合法的场合中所取得纯粹一致的拘束力。我们不能说这种根据于道德进步路线的历史顺序,是明显地错误的,但为慎重起见,我们必须承认要证实其一切细节,现有的证据显然并不充分。事实正如我们常常指出来的那样,罗马人在有关合意
Franc.She 9
220330671.doc
的法律方面是独特地凭经验的,他们从来没有发展一个令人满意的和不矛盾的真正作为契约的契约理论,他们的市民法要因(causa civilis)学说,被假定为是一切有拘束力的合意所依据的,是完全没有可靠的法律基础的。梅因留给我们的印象是,裁判官起着体现“能达到正当后果的‘诺成契约’原则”的‘裁判官告令”,把合意的可诉性扩大到几乎毫无限制。这是一种严重的夸大。实际上,裁判官告令,在数量上是很少的,在性质上是很专门的,在范围上是很狭小的。毫无疑义,到了古典时期,契约的领域在理论上和在实际上,都已变得很广泛,足以满足一切普通目的了;但是它还不能公正地被认为具有梅因这样热诚地归功于它的那种科学的均称性或道德的一致性。
在第五章的结尾,可以看到梅因对他所想象的“各国民事法律”的发展,进行了干练的总结,同时读者在开始阅读本书之前,最好先熟读这一段文字,即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研究过有关古代‘人法’的各个部分”开始的几页,并且先要把本书开头的主要的五章所依据的要旨牢记在心中。
这几页中最后一句话是全部英国法律文献中最著名的“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这些文句在它写成的当时,是适当的、可以接受的——那个时候,十九世纪个人主义的全部力量正在逐渐增加其动力。关于梅因所应用的“身分”这个字,是否适当,这里不拟作专门的详尽讨论,但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就他所接受的含义来讲,是有讨论的余地的;但他的结论实足以表现一条为当今历史法学家没有任何争执的原则——即个人自决的原则,把个人从家庭和集团束缚的罗网中分离开来;或者,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即从集体走向个人的运动。这是梅因的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他对所有那些先天的空想进行攻击的矛头,这些空想创造了抽象的人,作为年轻世界的天命的君主,这样就颠倒了全部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梅因在说这个运动到此处为止是进步社会的特征时,是很慎重的。现在有许多人在问,有的带着怀疑,有的可以看出是有礼貌地,究竟有没有从契约到身分的相反运动发生过。我们可以完全肯定,这个由十九世纪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安放在“契约自由”这神圣语句的神龛内的个人绝对自决,到了今日已经有了很多的改变;现在,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远较著作“古代法”的时候更广泛地受到特别团体、尤其是职业团体的支配,而他的进入这些团体并非都出于他自己的自由选择。很可能,过去一度由家庭这个发源地担任的任务,在将来要由工团这个发源地来担任了;也可能梅因的这个著名原则,将会有一天被简单地认为只是社会史中的一个插曲。如果竟然是这样发生了,这究竟是标志着社会的进步还是退化,是一个非常适合于每一个有思想的人仔细研究的问题,但在这里,是不宜于作任何讨论的。
本书中有些不重要的疏漏之处,对于一般读者,是可以不必特别提出的。但10 Franc.She
220330671.doc
有一点必须加以指出。在第四章中梅因竟以为布拉克顿(Bracton)曾“把全部形式和三分之一内容直接剽窃自‘民法大全’”的一篇论文,作为纯粹英国法的一个纲要,向其同胞推销。这与现在由麦特兰(Maitland)研究结果确定的事实严重地不相符合,这些事实,在1861年时是不可避免地被误解了。布拉克顿的亨利或布拉顿(Braton)是除了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外,一般人很少知道的一个作家,因此请原谅我为他作一介绍,他是亨利三世皇朝后半期中一个王室法庭的法官,并且是研究中世纪时期“英国法律和习惯”方面一个最重要的“寺院派”作家。像他当时所有的教士一样,他用拉丁文纂述文章,他应用罗马法的传统分类与排列;虽然决不至于有“三分之一内容”,但他的著名论文中确有相当部分借助于罗马法——但不是“民法大全”的本身,而是十二世纪“波罗诺学派”(Bolognese)注释者所“修正”的罗马法律学。但他的著作,不论在意图上或是在效果上,绝不是欺人之谈:他的主题是真实的、本土风光的、英国的封建法律,虽然曾受到当时所公认的研究法律学的方法——一个必然是罗马式的方法——的影响,而它受到这种影响,实在也是无可避免的。
最后必须加以说明,在本书中提到的一二椿有关英国法的事,最近已经有了变化。一般都知道,在梅因著作中占有非常显著地位的并且是他所一贯不赞成的长子继承权(priamogeniture),在现在,除了荣誉称号以外,在一切主要方面都已从英国继承法中消失了。第八章中有关英国动产法“威胁着要并吞和毁灭不动产法”的预言,现在大部已经实现了。
至于英国已婚妇女的无能力(第五章),这种现象在1861年时是任何文明社会的一种耻辱,在二十一年以后已被彻底消灭,这原是众所周知而毋庸加以说明的事。
喀莱顿·垦卜·亚伦(Carleton Kemp Allen)
19xx年
第01章、古代法典
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法律学制度从一部“法典”(Code)开始,也随着它而结束。从罗马法历史的开始到结束,它的释义者一贯地在其用语中暗示着,他们制度的实体是建筑于“十二铜表法”(Twelve Decemviral Tables)、因此也就是建筑于成文法的基础上的。在罗马,对于“十二铜表法”以前的一切制度,除了一特殊之点外,都不予承认。罗马法律学在理论上是来自一部法典,而英国法律在理论上则被认为是来自古代的不成文惯例,这是他们制度的发展和我们制度的发展所以不同的主要原因。这两种理论与事实不完全相符,但却都产生了极端重要的后果。
Franc.She 11
220330671.doc
“十二铜表法”的公布并不能作为我们开始研究法律史的最早起点,这是毋庸多说的。古代罗马法典,是属于这样一类的法典,几乎世界上每一个文明国家都可以提出一个范例,并且以罗马和希腊而论,它们是在彼此之间相距并不过分遥远的时代中在它们各自的领域中广泛地传布着。它们是在非常类似的情况下出现的,并且据我们所知,也是由类似的原因产生的。毫无疑问,在这些法典的后面,存在许多法律现象,这些法律现象在时间上是发生在法典之前的。现在有很多文件记录,明白地提供我们关于这种早期法律现象的知识。
但在语言学家能对“梵文”(Sanskrit)文学作出完全的分析以前,我们知识的最好来源无疑地只有希腊的荷马诗篇(Homeric poems),当然我们不能把它认作一种确实事件的历史,而只能把它作为作者所知道的不是完全出于想象的一种社会状态的描写。纵使诗人的想象力对于这种英雄时代的某些特征,如战士的勇猛以及神的威武,可能有些夸张之处,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的想象力曾受到道德或形而上学的概念的影响,因为,这些概念当时当没有作为有意识观察的对象。就这一点而论,荷马文学实远比后期的文件更为真实可靠,因为,这些文件虽然也是为了要说明同样的较早时期的情况,但是它们的编纂是在哲学的或神学的影响之下进行的。如果我们能通过任何方法,断定法律概念的早期形式,这将对我们有无限的价值。这些基本观念对于法学家,真象原始地壳对于地质学家一样的可贵。这些观念中,可能含有法律在后来表现其自己的一切形式。我们的法律科学所以处于这样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主要由于对于这些观念除了最最肤浅的研究之外,采取了一概加以拒绝的草率态度或偏见。在采用观察的方法以代替假设法之前,法学家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真和物理学与生物学中所用的调查研究方法十分近似。
凡是似乎可信的和内容丰富的、但却绝对未经证实的各种理论,像“自然法”(Law of Nature)或“社会契约”(Social Compact)之类,往往为一般人所爱好,很少有踏实地探究社会和法律的原始历史的;这些理论不但使注意力离开了可以发现真理的唯一出处,并且当它们一度被接受和相信了以后,就有可能使法律学以后各个阶段都受到其最真实和最大的影响,因而也就模糊了真理。
在荷马诗篇中,曾经提到“地美士”(Themis)和“地美士第”(Themistes)的字眼,这是一些最早期的概念,它们和现在已经充分发达的法律观念和生活规律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所周知,“地美士”在后期希腊万神庙中是“司法女神”(Godadess of Justice),但这是一个现代的并且已经很发达的观念,同“伊利亚特”(Iliad)中把“地美士”描写为宙斯(Zeus)的陪审官的原意,完全不同。所有对于人类原始状态的忠实观察者现在都能清楚地看到,在人类的初生时代,人们对于持续不变的或定期循坏发生的一些活动只能假用一个有人格的代理人来加以说明。这样,吹12 Franc.She
220330671.doc
着的风是一个人,并且当然是一个神圣的人;上升、上升、到达极顶然后下落的太阳是一个人,并且是一个神圣的人;生长庄稼的土地是一个人,也是神圣的人。在物理世界中如此,在道德世界中也是如此。当国王用判决解决纠纷时,他的判决假设是直接灵感的结果。把司法审判权交给国王或上帝的神圣代理人,万王之中最伟大的国王,就是地美士。这个概念的特点,表现在这个字的复数用法。地美士第,即地美西斯,是“地美士”的复数,意指审判的本身,是由神授予法官的。在谈到国王时,好像他们的手中就有着丰富的“地美士第”,随时可以应用似的。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了解“地美士第”并不就是法律而是判决。格罗脱(Grote)先生在其“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中说,“宙斯或是地球上的人王,不是一个立法者而是一个法官”。他有充足的“地美士第”,但是,虽然始终相信“地美士第”来自天上,我们却并不能就假设在各个“地美士第”之间,有着任何一条原则贯串着;它们是各别的、单独的判决。
甚至在荷马诗篇中,我们也还可以看出,这些观念只是暂时的。在古代社会的简单机构中,情况类似的情形可能比现在还要普遍,而在一系列的类似案件中,就有可能采用彼此近似的审判。我们由此就有了一种“习惯”的胚种或者雏形,这是在“地美士第”或判决的概念之后的一种概念。由于我们的现代联想,我们就先天地倾向于以为一个“习惯”观念必然是先于一个司法判决的概念,以为一个判决必然是肯定一个“习惯”,或是对于违犯“习惯”的人加以处罚,纵使我们的思想倾向是这样,但是,非常明确,各种观念的历史顺序却真正是象我在前面所排列的那样排列的。荷马对于一个在胚胎中的习惯,有时用单数的“地美士”——更多的时候则用“达克”(Dike),它的意义明显地介于一个“判决”和一个“习惯”或“惯例”之间。至于NFμσ是指一条“法律”,这是后期希腊社会政治语言中一个非常伟大而著名的名辞,但在荷马诗篇中却没有见到过。
所谓神圣的代理人这种观念,暗示着“地美士第”,而其本身又人格化在“地美士”中。这种观念一个肤浅的研究者可能会把它和其他原始信念混淆起来,我们必须把它们区分开来。有一种概念认为整部的法典是由“神”(Deity)口授的,例如印度的“摩奴”法典(Hindoo laws of Manu),这种概念似乎属于比较后期和比较发达的思想,“地美士”和“地美士第”是同长久以来顽固地为人们拘泥着的一种信念密切地联系着的,这种信念认为在生活的每一个关系中,在每一个社会制度中,都有一种神的影响作为它的基础,并支持着它。在每一古代法律中,在每一政治思想的雏形中,到处都可以遇到这种信念的征象。那时候所有的根本制度如“国家”、“种族”和“家族”都是假定为贡献给一个超自然的主宰,并由这个主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在这些制度所包含的各种不同关系中集合起来的人们,必然地要定期举行公共的祭礼,供奉公共的祭品,他们时时为了祈求赦免因无意
Franc.She 13
220330671.doc
或疏忽的侮慢而招惹的刑罚举行着斋戒和赎罪,在这中间这种同样的义务甚至被更有意义地承认着。凡是熟悉普通古典文学的人,都会记得家祭(sacra gentilicia)这个名词,这对于古代罗马的收养法和遗嘱法都有着极重要的影响。到现在为止,还保存着原始社会某些最古怪特点的印度习惯法(Hindoo Customary Law),对于人们所有的一切权利和继承的一切规定,几乎都要在死人安葬时,也就是说在家族延续发生中断时,按照举行规定仪式时的严肃程度而决定。
在我们离开这一法律学阶段以前,凡是英国学生都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一点。在边沁的“政府论丛”(Fragment on Government),以及奥斯丁的“法律学范围论”(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中,他们把每一项法律分解为立法者的一个命令,因此是一种强加于公民身上的义务,并且是在发生反抗时的一种制裁;他们并且进一步断定这个作为法律第一个要素的命令,必须不仅是针对一个单一的行为,而且是对着一系列的或者许多属于同一类型和性质的行为。
可以断言,在人类初生时代,不可能想象会有任何种类的立法机关,甚至一个明确的立法者。法律还没有达到习惯的程度,它只是一种惯行。用一句法国成语,它还只是一种“气氛”。对于是或非唯一有权威性的说明是根据事实作出的司法判决,并不是由于违犯了预先假定的一条法律,而是在审判时中一个较高的权力第一次灌输入法官脑中的。我们要想理解这些在时间上和在联想上同我们距离这样遥远的种种见解,当然是极端困难的,但是,我们如果能比较详细地研究一下古代社会的构成,了解到在古代社会中,每个人的生命有极大部分都生活在族长的专制之下,他的一切行为实际上不是由法律的而是由翻复无常的一种统治所控制着,这就比较可信了。我可以说,一个英国人应该比外国人更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即“地美士第”的发生先于任何法律概念,这是因为,在流行着的有关英国法律学性质的许多相互矛盾的理论中,其最得人心的,或者无论如何是最能影响实践的,当然是假定成案和先例先于规则、原则及差别而存在的理论。应该指出,根据边沁和奥斯丁的见解,“地美士第”还有把单一的或唯一的命令从法律中区分开来的特性。真正的法律使所有公民毫无差别地一致遵守着种类相似的许多条例;这正是法律的最为一般人所深切感觉到的特征,使“法律”这个名词只能适用于一致、连续和类似。至于命令只规定一个单独的行为,因此同“地美士第”比较近似的是命令而不是法律。命令只是对孤立的事实状态的宣告,并不必然地按照一定的顺序一个和另一个相近。
这样把法律的各种要素加以分析的结果,同已经成熟的法律学的事实完全相符;并且只要在用语上稍为引伸一下,它们就能在形式上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各个时代的一切法律。但是,这并不就是说,在这个概括中所含有的法律观念,即使到现在,还完全同这个解剖相符合;可奇怪的是,我们对于古代思想史如果研14 Franc.She
220330671.doc
究得越深入,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同边沁所主张的所谓法律是几个要素的混合物的这种概念,距离越远。
英雄时代的文学告诉我们的法律萌芽,一种是“地美士第”,还有一种是在稍为发展的“达克”的概念中。我们在法律学史上达到的下一个阶段是非常著名的,并且也是饶有兴趣的。格罗脱先生在其“希腊史”第二篇第二章中,曾把已逐渐不同于荷马所纂绘的社会生活方式详细加以描写。英雄时代的王权,部分地依靠着神所赋与的特权,部分地依靠着拥有出类拔萃的体力、勇敢和智慧。逐渐地,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印象开始淡薄,当一系列的世袭国王中产生了柔弱无能的人,王家的权力就开始削弱,并且终于让位于贵族统治。
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地应用革命的术语,则我们可以说,王位是被荷马一再提到的和加以描写的领袖议会所篡夺了。无论如何,在欧洲各地,这时已经从国王统治时代转变到一个寡头政治时代;即使在名义上,君主职能还没有绝对消失,然而王权已缩小到只剩下一个暗影。他成为只是一个世袭将军,像在拉栖第梦(Lacedemon),只是一个官吏,像雅典的执政王(King Archon at Athens),或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祭司,像罗马的献身王(Rex Sacrieiculus)。在希腊、意大利和小亚细亚,统治阶级似乎一般都包括着由一种假定的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许多家族,他们虽然在开始时似乎都主张有一种近似神圣的性质,但他们的力量在实际上却并不在于他们所标榜的神圣性。除非他们过早地被平民团体所推翻,他们都会走向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一种贵族政治。在更远一些的亚洲国家,社会所遭遇的变革,在时间上,当然要比意大利和希腊所发生的这些革命早得多;但这些革命在文化上的相对地位,则似乎是完全一样的,并且在一般性质上,它们也似乎是极端相似的。有些证据证明,后来结合在波斯王朝统治下的各个民族以及散居在印度半岛上的各个民族,都有其英雄时代和贵族政治时代;但是在它们那里,分别产生了军事的寡头政治和宗教的寡头政治,而国王的权威则一般并没有被取而代之。同西方事物的发展过程相反,在东方,宗教因素有胜过军事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倾向。在国王和僧侣阶级之间,军事和民事的贵族政治消失了,灭绝了,或者微不足道;我们所看到的最后结果,是一个君主享有大权,但是受到了祭司阶级的特权的拘束。在东方,贵族政治成为宗教的,而在西方,贵族政治成为民事的或政治的,虽然有着这些区别,但是,在一个英雄国王历史时代的后面跟着来了一个贵族政治的历史时代,这样一个命题是可以被认为正确的,纵使并不对于全人类都是如此,但无论如何,对于印度—欧罗巴(Indo—European)系各国是一概可以适用的。
有一点对于法学家很重要,就是这些贵族都是法律的受托人和执行人。他们似乎已经继承了国王的特权,唯一的重要区别,在于他们并不对每一个判决都装
Franc.She 15
220330671.doc
作出于直接的神示。
主张全部法律或是部分法律来自神授的思想联系,仍旧到处表现出来,这使族长所作的判决被诿诸于超人类的口授,但是思想的进步已不复允许把个别争议的解决,用假定一种超人的仲裁来解释。法律寡头政治现在所主张的是要垄断法律知识,要对决定争论所依据的各项原则有独占的权利。我们在事实上已到了“习惯法”的时代。“习惯”或“惯例”现在已成为一个有实质的集合体而存在,并被假定为贵族阶层或阶级所精确知道的。我们所依据的权威使我们深信,这种寄托于寡头政治的信任有时不免要被滥用,但这当然不应该仅仅视为一种僭取或暴政的手段。在文字发明以前,以及当这门技术还处于初创时代,一个赋与司法特权的贵族政治成了唯一的权宜手段,依靠这种手段可以把民族或部族的习惯相当正确地保存着。正是由于它们被托付于社会中少数人的记忆力,习惯的真实性才能尽可能地得到保证。
“习惯法”以及它为一个特权阶级所秘藏的时代,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法律学处于怎样一个状态,其残留痕迹到现在仍旧可以在法律的和民间的用语中发现。这种专门为有特权的少数人所知道的法律,不论这少数人是一个等级,一个贵族团体,一个祭司团体,或者一个僧侣学院,是一种真正的不成文法。除此以外,世界上就没有所谓不成文法这样东西了。英国的判例法有时被称为不成文法,有些英国理论家正告我们说,如果真要编订一部英国法律学的法典,我们必须把不成文法变为成文法——他们坚持说,这一个转变,如果不是在政策上有可疑之处,无论如何,是非常重大的。实际上,在有一个时期中,英国普通法的确可以合理地称为不成文法。前一辈的英国法官们确实标榜着具有为法院和人民群众所不完全知道的规则、原则及差别的知识。他们要垄断的法律,究竟是不是完全不成文的,是非常可疑的。
但是,无论如何,纵使可以假定过去确实曾经一度有着许多专门为法官们所知道的民事和刑事规则,但它在不久以后即已不再成为不成文法了。在“威斯敏斯特法院”(Courts at Westminster Hall)开始根据档案,不论是根据年鉴或是其他资料作出判决时,他们所执行的法律已是成文法。到这个时候英国法律中任何一条规则,必须首先从印成的许多判决先例所记录的事实中清理出来,然后再由特定法官根据其不同的风格、精确度以及知识而表现于不同的文字形式中,最后再把它运用于审判的案件。在这过程中,没有一个阶段显示出有任何特点,使它和成文法有什么不同之处。英国法律是成文的判例法,它和法典法的唯一不同之处,只在于它是用不同的方法写成的。
离开“习惯法”时代,我们再来谈谈法律学史上另一明确划分的时代,也就是“法典”时代,在那些古代法典中,罗马的“十二铜表法”是最著名的范例。16 Franc.She
220330671.doc
在希腊、在意大利、在西亚的希腊化海岸上,这些法典几乎到处都在同一个时期出现,这所谓同一个时期,我的意思当然并不是指在时间上的同一个时期,而是说在每一个社会相对地进步到类似的情况下出现的。在我所提到的几个国家中,到处都把法律铭刻在石碑上,向人民公布,以代替一个单凭有特权的寡头统治阶级的记忆的惯例。在我所说的这种变化中,我们决不能设想当时已有了现代编纂法典时所必须有的各种精密考虑。毫无疑问,古代法典的所以会创造成功是由于文字的发现和传布。
诚然,贵族们似乎曾经滥用其对于法律知识的独占:并且无论如何,他们对于法律的独占有力地阻碍了当时在西方世界开始逐渐普遍的那些平民运动获得成功。不过虽然民主情绪可能使这些法典更加深得人心,但是法典的产生当然主要还是由于文字发明的直接结果。铭刻的石碑被证明真是一种比较好的法律保存者,并且是一种使其正确保存的更好保证,这比仅仅依靠着少数人的记忆要好得多,虽然这种记忆由于惯常运用的结果也是在不断地加强着的。
罗马法典就是属于上面所说的那一类法典,这类法典的价值不在于其分类比较匀称或用词比较简洁明了,而在于它们为众所周知,以及它们能使每个人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和不应该做些什么的知识。罗马“十二铜表法”中确实显示出有排列匀稀的某种迹象;但根据传说,这可能是由于当时这个法律的编纂者曾求助于希腊人,这些希腊人具有后期希腊在编纂法律工作上的经验。从“梭伦的阿提喀法典”(Attic Code of Solon)所遗留下来的片断,可以看到它很少有秩序,而在“德里科”的法律(Laws of Draco)中也许更少。
这些东方的和西方的法典的遗迹,也都明显地证明不管它们的主要性质是如何的不同,它们中间都混杂着宗教的、民事的以及仅仅是道德的各种命令;而这是和我们从其他来源所知道的古代思想完全一致的,至于把法律从道德中分离出来,把宗教从法律中分离出来,则非常明显是属于智力发展的较后阶段的事。
但是,不论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这些“法典”的特点是什么,它们对于古代社会的重要性,是无法用言词来形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影响着每一个社会的全部将来——并不在于究竟该不该有一个法典,因为大多数古代社会似乎迟早都会有法典的,并且如果不是由于封建制度造成了法律学史上重要的中断,则所有的现代法律很可能都将明显地追溯到这些渊源中的一个或一个以上上去。但是民族历史的转折点,是要看在哪一个时期,在社会进步的哪一个阶段,他们应该把法律书写成为文字。在西方世界中每一个国家的平民成分都成功地击溃了寡头政治的垄断,几乎普遍地在“共和政治”史的初期就获得了一个法典。但是在东方,像我已在前面说过的,统治的贵族们逐渐倾向于变为宗教的而不是军事的或政治的,并因此不但不失去反而获得了权力;同时,在有些事例中,亚细亚国家的地
Franc.She 17
220330671.doc
理构造促使各个社会比西方社会的面积更大,人口更多;根据公认的社会规律,一套特定制度传布的空间越广,它的韧性和活力也越大。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东方各国社会编制法典,相对地讲,要比西方国家迟得多,并且有很不相同的性质。亚细亚的宗教寡头,或者是为了他们自己参考,或者是为了帮助记忆,或者是为了教育生徒,都终于把他们的法律知识具体地编订成为法典;但也许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最难于拒绝的诱力,还在于这是一个可以增加和巩固他们影响的机会。他们完全垄断法律知识,这一点使它们能用汇编来欺骗世人,而汇编中所包括的确实已被遵守的规则,还不及祭司阶级认为应当被遵守的规则多。称为“摩奴”法律的印度法典,当然是婆罗门(Brahmin)所编辑的,无疑地包含了印度民族的许多真正的惯例,但根据现代最好的东方学者的见解,整个讲起来,它并不代表确实曾经在印度斯坦执行过的一套规则。在它里面有一大部分只是在婆罗门的眼光中应该作为法律的一幅理想图画。这是和人类的性质相适应的,也是和作者的特殊动机相一致的:即像“摩奴法典”这样的一些法典,应该假托为最古的,并且应认为完全从“神”得来的。按照印度的神话学,“摩奴”是至尊“上帝”的一种分出物;但是这个冠以他的名称的汇编,虽然其确切日期已不易查考,从印度法律学的相对进步来看,实在是一种近代的产品。
“十二铜表法”以及类似的法典赋予有关社会的好处,主要是保护这些社会使它们不受有特权的寡头政治的欺诈,使国家制度不致自发地腐化和败坏。“罗马法典”只是把罗马人的现存习惯表述于文字中。从罗马人在文化进步中的相对地位来看,它是一非常早的法典,而它公布的时间,正当罗马社会还没有从这样一种智力状态中脱身出来,也就是正当他们的智力状态还处在政治和宗教义务不可避免地混淆在一起的时候。一个野蛮社会实行的一套习惯,往往对其文化进步绝对有害或有某种特殊的危险。一个特定社会从其初生时代和在其原始状态就已经采用的一些惯例,一般是一些在大体上最能适合于促进其物质和道德福利的惯例;如果它们能保持其完整性,以至新的社会需要培养出新的惯行,则这个社会几乎可以肯定是向上发展的。但不幸的是,发展的规律始终威胁着要影响这些不成文的惯例。习惯是为群众所遵守的,但他们当然未必能理解它们所以存在的真正原因,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创造出迷信的理由以说明它们的永恒存在。
于是就开始着这样一种过程,简单地讲,就是从合理的惯例产生出不合理的惯例。类比,这是法律学成熟时期中最有价值的工具,但在法律学的初生时代却是最危险的陷阱。禁令和命令在开始时由于正当理由原来只限于某一种性质的行为,后来就被适用于属于同一类别的一切行为,因为一个人做了一椿要受到上帝谴责的行为,他在做任何稍有些类似的行为时,就必然地要感到一种自然的恐惧。当一种食物由于卫生的理由被禁止,禁令就要适用于一切类似的食物,虽然类比18 Franc.She
220330671.doc
在有的时候完全是建筑在想象的基础上的。同样的,为了保证一般清洁而作出的明智的规定,终于竟变成了教仪上净身的冗繁的手续。又如等级的划分是在社会史上特定紧急关头为保持民族生存所必需的,但逐渐退化而成为所有人类一切制度中最不幸的和最有损害的制度——“族籍制度”(Caste)。印度法的命运,在事实上,是衡量罗马法典价值的尺度。人种学告诉我们,罗马人与印度人来自同一个原始祖先,而在他们的原来习惯中,也确实有显著的类似之处,即使在现在,印度法律学还存留着考虑周到和判断正确的实体,只是不合理的摹仿已使它在实体上面附加着残酷妄诞的巨大附着物。罗马人由于得到了法典的保护,没有受到这一类腐蚀。在它编纂的时期,惯例还是很健康的,如果推迟到一百年以后,或许就太迟了。印度法的大部分是具体规定于文字中的,但是,在“梵文”中到现在仍旧保存着的撮要虽然在一种意义上是很古的,但在它们中间有充分证据,证明它们的编制是在错误造成之后。当然,我们不能就因此而有权利说,如果“十二铜表法”没有公布,罗马人的文明将像印度文明那样地无力和恶化,但至少这是可以断定的,他们有了法典,才避免了那样不幸的遭遇。
第02章、法律拟制
当原始法律一经制成“法典”,所谓法律自发的发展,便告中止。自此以后,对它起着影响的,如果确有影响的话,便都是有意的和来自外界的。我们不能设想,任何民族或部族的习惯,从一个族长把它们宣告以后一直到把它们用文字公布为止在这一个长久的——在有些情况下,非常悠久的——期间内,会一无变更。如果认为在这个期间以内的任何变更都不是有意地进行的,也是不妥当的。但就我们对于这个时期内法律进步所掌握的一些知识来说,我们确有理由假定,在造成变化中,故意只占着极小的部分。远古惯例中曾经发生过一些改革,但促使这些改革发生的情感作用和思想方式,却不是我们在现在智慧状态下所能理解的。但是,有了“法典”就开始了一个新纪元。在这时期以后,当我们追溯一下法律变更的经过时,我们就能发现这些变更都是出于一种要求改进的、有意识的愿望,或者无论如何,是出于一种具有一定目的的有意识的愿望,这同原始时代所企求的完全不同。
初看起来,我们从法典产生以后的法律制度史中,似乎很难引伸出来足以深信不疑的各种一般命题。涉及的领域是太广泛了。我们很难肯定,在我们的观察中是否已包括了足够数量的现象,或者我们对于所观察的现象,是否已有了正确的理解。但如果我们注意到,在法典时代开始后,静止的社会和进步的社会之间的区分已开始暴露出来的事实,我们的工作就比较容易进行。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进步的社会,而这类社会显然是极端少数的。虽然有着充分的证据,但是对于一
Franc.She 19
220330671.doc
个西欧的公民,还是非常难于使他完全领会这样一个真理,即环绕在他周围的文明,在整个世界史中,实在是一个罕有的例外。如果把各个进步民族同人类生活总体的关系鲜明地放在我们的前面,则我们中间共有的思想感情,我们所有的一切希望、恐惧和理想必将受到重大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辩的,几乎绝大部分的人类,在其民事制度因被纳入某种永久纪录中而第一次使其具有外表上的完善性时,就绝少有表示要再加以改进的愿望。一套惯例有时被另外一套惯例强暴地推翻和代替了;到处,标榜着来自超自然渊源的一个原始法典,往往由于僧侣注释者的牵强附会而被大大地扩大了,并被歪曲成为最可惊人的形式;但是,除了世界上极小部分外,从没有发生过一个法律制度的逐渐改良。世界有物质文明,但不是文明发展法律,而是法律限制着文明。研究现在处在原始状态下的各民族,使我们得到了某些社会所以停止发展的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婆罗门教的印度还没有超过所有人类各民族历史都发生过的阶段,就是法律的统治尚未从宗教的统治中区分出来的那个阶段。在这类社会中的成员,认为违犯了一条宗教命令应该用普通刑罚来处罚,而违背了一个民事义务则要使过失者受到神的惩戒。在中国,这一点是过去了,但进步又似乎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在它的民事法律中,同时又包括了这个民族所可能想象到的一切观念。静止的和进步的社会之间的差别,是还须继续加以探究的大秘密之一。在对于它的局部的解释中,我敢把上章之末所提出的意见,提供考虑。我也许必须进一步说明,如果不明白地理解到,在人类民族中,静止状态是常规,而进步恰恰是例外,这样研究就很少可能有结果。成功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对于罗马法的所有各主要阶段,都要有精确的知识。罗马法律学中,有着任何一套人类制度中最长久著名的历史。它所经历的一切变化的性质,已经在大体上得到很好的肯定。从它的开始到它的结束,它是逐步地改变得更好,或向着修改者所认为更好的方向发展,而且改进是在各个时期中不断地进行着的,在这些时期中,所有其余的人类的思想和行动,在实质上都已经放慢了脚步,并且不止一次地陷于完全停滞不前的状态。
我将把我的叙述局限于进步社会中所发生的情况。关于这些社会,可以这样说,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的前面的。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接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所谈到的社会是进步的,人民幸福的或大或小,完全决定于缺口缩小的快慢程度。
关于使“法律”和社会相协调的媒介,有一个有些价值的一般命题可以提出。据我看来,这些手段有三,即“法律拟制”、“衡平”和“立法”。它们的历史顺序就像我在上面所排列的,有时,其中两个在同时进行,也有些法律制度没有受到它们中的这一个或另一个的影响。但我从没有看到过一个例子,它们出现的顺序20 Franc.She
220330671.doc
会是不同的或颠倒过来的。“衡平”的早期历史,一般讲起来,都是比较模糊的,因此,有人以为某些改进民法的单独条例,就早于任何衡平的审判权。我的意见是,不论任何地方,补救的“衡平”必早于补救的立法;但是,倘使事实上并不严格地是这样,那就只须把关于它们先后顺序的命题局限于那些时期,即,它们在改变原始法律中发生持续和实质影响的时期内。
我在应用“拟制”这个字时,其含意比英国法学家习用的意义要广泛一些,比罗马的“拟制”(fictiones)则要广泛得多。“拟制”(fictio)在旧罗马法中,恰当地讲,是一个辩诉的名词,表示原告一方的虚伪证言是不准被告反驳的;例如原告实际上是一个外国人而提出他是一个罗马公民的证言即是。这种“拟制”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给予审判权,因此,他们与英国后座法院和理财法院命令状中的主张非常类似,这些法院就是通过这些主张来剥夺普通诉证的审判权的;——主张被告已为国王执行官所拘留,或是主张原告为国王的债务人,并以被告的拖欠为理由而不能清偿债务。
但我现在应用“法律拟制”这一个用语,是要用以表示掩盖、或目的在掩盖一条法律规定已经发生变化这事实的任何假定,其时法律的文字并没有被改变,但其运用则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个用语包括了上面我从英国法和罗马法中所引证的拟制的实例,但是它们所包括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因为我认为英国的“判例法”和罗马的“法律解答”(Responsa Prudentium)都是以拟制为其基础的。这两方面的例子立刻就要加以研究。事实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法律都已经完全被变更了;而拟制是它仍旧和改变以前一样。为什么各种不同形式的拟制特别适合于社会的新生时代,这是不难理解的。
它们能满足并不十分缺乏的改进的愿望,而同时又可以不触犯当时始终存在的、对于变更的迷信般的嫌恶。在社会进步到了一定阶段时,它们是克服法律严格性最有价值的权宜办法。真的,如果没有其中之一,即“收养的拟制”,准许人为地产生血缘关系,就很难理解社会怎样能脱出其襁褓而开始其向文明前进的第一步。因此,我们不应该受着边沁的影响,他一遇到法律拟制就要加以嘲笑谩骂。他认为拟制只是诈骗,这适足以说明对于它们在法律发展史中所担任的特殊任务,愚昧无知。但同时有些理论家看到了拟制的用处,即据而认为它们应该在我们制度中固定下来,如果我们同意他们的见解,也同样的是愚蠢的。它们有它们的时代,但是它们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们现在已不值得要去用像法律拟制这样一种粗糙的方式以求达到一个公认为有益的目的。我不能承认任何变例都是合法的,如果它只有使法律更难解,或者是更难按照和谐的顺序排列起来,因为,法律拟制是均称分类的最大障碍。法律制度仍旧保持原样,原封不动,但它已只成为一个躯壳。它已经早被破坏了,而藏在其外衣里面的则是新的规定。于是,困难就
Franc.She 21
220330671.doc
立刻发生了,我们将很难断定,实际上可以适用的规定究竟应该归类于其真正的还是归类于其表面的地位,同时,禀性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部门中进行选择时,也将得到不同的结果。如果英国法真要得到有秩序的分门别类,那就必须剪除这些法律拟制,虽然最近在立法上有所改进,但在英国法律中,拟制仍旧是很多的。
法律用以适应社会需要的其次一个手段,我称之为“衡平”(Equity)。这个名词的含义,是指同原有民法同时存在的某一些规定,它们建筑在各别原则的基础上,并且由于这些原则所固有的一种无上神圣性,它们竟然可以代替民法。不论是罗马的“裁判官”或是英国的大法官的“衡平”,同出现比较早的“拟制”都有不同,其不同之点在于它能公开地、明白地干涉法律。另一方面,它又和“立法”不同,这是发生在它之后的另外一种法律改进的媒介,其不同之点在于它的权力基础并不建筑在任何外界的人或团体的特权上面,甚至也不建筑在宣布它的官吏的特权上面,而是建筑在它原则的特殊性上面,这些原则,据说是一切法律应该加以遵循的。这种认为有一套原则比普通法律具有更高的神圣性并且可以不经任何外界团体的同意而主张单独适用的概念,要比法律拟制最初出现时属于进步得多的一个思想阶段。
最后一个改进的手段是“立法”(Legislation),就是由一个立法机关制定的法规。这种立法机关,不论它的形式是一个专制君主或是一个议会,总之是一个为社会所公认的机关。
它和“法律拟制”不同,正像“衡平”和“法律拟制”不同一样。它和“衡平”也有不同,因为它的权威来自一个外界团体或人。它所以有强制力,与其原则无关。不论社会舆论对立法机关加以任何现实的约束,在理论上,它有权把它所认为适宜的义务加在社会的成员身上。没有谁能够限制它任意制定法律。如果衡平的名词可以用作是或非的标准,而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规恰巧是根据了这些标准而调整的,则立法可以说是根据了衡平而制定的;但即使是这样,这些法规所以能有拘束力,仍旧是由于立法机关本身的权力,并不是由于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所根据的原则的权力。因此,它们在专门术语的意义上与“衡平法”不同,后者标榜着有一种高度的神圣性,这使它们即使没有经过君主或议会同意,也应该为法院立即承认。这些差别特别重要,因为一个边沁的学生很容易把“拟制”、“衡平”和“制定法”混淆起来,把它们统统归属于立法的一个项目下。他会说,它们都包括制定法律;它们之所以不同,只是在新法律产生的机构。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但这并不使我们有理由不去利用这样一个便利的名词,表达出立法的特殊意义。
“立法”与“衡平”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和在大多数法律家的心目中,是分开的;我们决不能忽略它们之间的区分,纵使是习惯上的区分,因为这个区分有着22 Franc.She
220330671.doc
重要的实际后果。
法律拟制的例子,几乎可以很容易地在任何正常发展的法律规定中找到,因为它们的真正性质立刻可以为现代观察者所发觉。在我即将进而研究的两个例子中,其所用权宜的性质不是很容易立刻就发现的。这些拟制的第一批作者,其目的也许并不在改革,当然更不希望被人怀疑是在改革。此外,有一些人,并且是始终有着这样一些人,拒绝看到在发展过程中的任何拟制,而习惯言语证实了他们的拒绝。因此,没有其他的例子能够被更好地用来说明法律拟制的分布广泛,以及它们在完成其双重任务,即一方面改变一个法律制度,而另一方面又掩盖这种改变时所有的效率。
我们在英国惯常看到有一种机构,在扩大、变更和改进法律。但在理论上这种机构原是不能改变现存法律一丝一毫的。这种用以完成实际立法工作的过程,并非是不可感知的,只是不被承认而已。关于包括在判例中和记录在法律报告中的我们大部分的法律制度,我们习惯于用一种双重言语,并往往持有一种双重的互不一致的两套观念。当有一些事实被提出于英国法院请求审判时,在法官与辩护人之间进行讨论的全部进程中,决不会、也决不可能提出要在旧的原则之外应用其他任何原则,或者除早已允许的差别外应用任何差别的问题。被绝对地认为当然的,是在某些地方,必然会有这样一条法律能够包括现在诉诸法律以求解决的事实,如果不能发现这样一条法律,那只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耐性、知识或智力把它发现而已。但是一当判决被宣告并列入纪录以后,我们就不自觉地、不公开地潜入到一种新的言语和一串新的思想中。到这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新的判决已经改变了法律。如果我们用有时被应用的一个非常不正确的说法,那就是可以适用的规定已经成为比较有弹性的了。
事实上,它们已经发生变化。在已有的先例中,现在已显然地多了一条,比较各个先例而得出的法律准则,必将和仅仅从一个例子所能得到的法律准则完全不同。旧的规定已经被废除,而一个新的规定已被用来代替它,但这个事实往往不容易觉察,因为我们不习惯于把我们从先例中引伸出来的法律公式用正确的文字表现出来,因此,它们性质的改变,除非是剧烈而明显的以外,就不很容易被发觉了。我现在不打算停下来详细讨论使英国法学家同意这些古怪变例的原因。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即原来可能有一条公认的学说,认为在某些地方,在太虚幻境中(in nubibus)或者在官吏的胸怀中(in gremio magistratum),有着一套完全的、有条理的、匀称的英国法律,其内容广泛,足以提供各种原则以适用于任何可以想象到的一组情况。这个理论在当初比在现在更为人们深信不疑,并且这也许真正有很好的根据。十三世纪的法官们也许的确掌握着一些为律师和一般人民所不知道的法律宝藏,因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秘密地从罗马法和“寺院法”的流行纲
Franc.She 23
220330671.doc
要中任意地但不一定是始终聪明地套用着一些东西。但是当韦斯敏斯德法院所判决的问题逐渐增加,足以组成一个独立存在的法律制度基础时,这个仓库就被封闭;而现在,几世纪以来,英国法律学者竟然提出了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命题,认为除“衡平法”和“制定法”以外,在英国法的基础上,从它第一次形成的时候起,就没有什么东西加上去过。我们不承认我们的法庭从事于立法工作;我们暗示着,它们从来没有做过立法工作;然而我们又主张,英国普通法的规定,在衡平法院和国会的帮助下,是可以同现代社会的复杂利益相适应的。
在罗马有一种法律,具有非常类似我们判例法中我所说的那些特点的,称为“法律解答”,即“法学家的回答”。这些“解答”的形式,在罗马法律学的各个时期中有极大的不同,但自始至终它们都是由对权威文件的注解组成的,而在最初,它们只是解释“十二铜表法”的各种意见的专门性的汇编。同我们一样,在这些解答中所有的法律用语都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即古代“法典”的原文应被保存不变。这就是明白的规定。它废止了一切注解和评注,并且不论解释者是如何的优秀,对于法典的任何解释,在参照古老的原文时,没有人敢公开承认,他所作的解释不会发生修正。但在事实上,冠以重要法学专家(jurisconsults)名字的“法律解答汇编”(Books of Responses),至少具有与我们报告案件同样的威权,并且不断地变更、扩大、限制或在实际上废弃“十二铜表法”的规定。在新法律学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它的作者们自认为非常专心地尊重着“法典”的原来文字。他们只是在解释它,阐明它,引伸其全部含义;但其结果,通过把原文凑合在一起,通过把法律加以调整使适应于确实发生的事实状态以及通过推测其可能适用于或许要发生的其他事实状态,通过介绍他们从其他文件注释中看到的解释原则,他们引伸出来大量的多种多样的法律准则,为“十二铜表法”的编纂者所梦想不到的,并且在实际上是很难或者不能在其中找到的。法学专家的全部论文都受到尊重,因为它们是被假定为完全符合“法典”的,但它们的相当高的权威是植基在把它们公诸于世的各个法学专家的声望上的。凡是举世公认为伟大的任何名字,必使一本“法律解答汇编”具有一种不小于立法机关制定法规所有的拘束力;而这样一本汇编的本身又成为更进一步的法律学所根据的新基础。但是,早期法学家的“解答”并不由原著者像现在那样印行的。它们由其学生加以记录和编辑,因此,多半都不是按照任何分类方法排列的。学生们在这些出版物中所处的地位,应加特别注意,因为他们对老师服务,一般都因老师对学生孜孜不倦的教育而得到补偿。被称为“法学教典”或“评释”(Commentaries)的教育论文为当时承认的义务的一种后来果实,是罗马制度中最显著的特色之一。至于法学专家们公诸于世的他们的分类法以及他们对于变更和改进专门术语的建议,显然不是在他们用以训练法学家的解答中,而是在这些涉及原理的作品中。
24 Franc.She
220330671.doc
在把罗马的“法律解答”同英国法律中最相近的相应部分进行比较时,我们必须牢记着,说明罗马这一部分法律学的权威者不是法院而是律师。罗马法庭的判决虽然在特定案件中是终局的判决,但除了当时承审官吏在职位上极有威信者外,并无使它可以适用于其他案件的权力。更确当地讲,在共和时期内罗马并没有和英国法院、日耳曼帝国审判院或法兰西君主国高等审判厅相类似的机构。罗马有许多高级官吏在其各该部门中都握有重要的司法职能,但他们的官职任期只有一年,因此它们不能与一个永久的裁判所相比,只能作为在律师领袖中间迅速地流转着的一个循环职位。对这种奇特状态的来源,可能有很多的说明,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可惊的变例,但是事实上,它比我们自己的制度更能适合于古代社会精神,因为这种社会常常不断地分裂为许多各别的阶级,在它们之间虽然互不往来,但却都不愿在他们上面有一个职业的教阶组织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度并没有产生某种很可能会产生的结果。例如,它并没有使罗马法通俗化——它没有像有些希腊共和国那样削弱知识分子精通这门科学所需要的努力,虽然并没有人为的障碍阻碍其普及和作权威的解释。相反的,如果不是由于其他许多原因在发生作用,那就非常可能,这种罗马法律学就会成为琐细、专门和难以解释的东西,像从那时候起流行着的任何制度一样。其次,另外有一种可能更加自然地预期会发生的后果,却没有在任何时期中表现出来。
直到罗马的共和政权被颠覆时,法学专家还只是一个界限不十分明显并在数量上有很大消长的阶级;虽然,他们之中任何特定的个人,对于在他们面前提出的任何案件能发表终局的意见,则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疑问。在拉丁文学中,有大量的关于著名法学专家日常活动的生动描写——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的当事人在清晨到达他的接待室,他的学生环立在周围,手里都拿着笔记簿,记录着这伟大法学家的回答——但这样描写的著名人物在任何既定时期内,很少或从来没有超过一个或二个人的。同时正由于当事人和辩护人的直接接触,罗马人民也就似乎经常注意着职业威信的升降。现在有充分的证据,特别是在西塞罗(Cicero)的著名演讲“为黑罗那辩”(Pro Murena)中,证明群众对于胜诉的重视往往不是不够而是过度的。
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在罗马法最早依靠了它而得以发展的这种手段中所发现的各种特点,就是使罗马法独特卓越的渊源,也是使它很早就能有丰富原则的渊源。原则的成长和茂盛,部分地是法律注释者之间的竞争所造成的,而这种竞争,在有法院的地方,即有国王或政府授以司法特权的受托人的地方,是不被人们所完全知道的。但是主要的媒介,无疑地还在于提请法律判决的各种案件的无限制地大量增加。
有些事实状态虽会使一个乡村当事人真诚地感到不知所措,但这些事实状态
Franc.She 25
220330671.doc
对于形成法学专家“解答”或法律判决基础的价值,还不如一个有才智的学生所提出的各种假设情况。成千成百的事实,不论是真的或是出于想象的,都被一律看待。
对于一个法学专家,如果他的意见为审判其当事人案件的官吏暂时废弃,他会毫不介意,除非这个官吏的法律知识或在专业上受到的尊敬都恰恰高过于他。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会完全不考虑其当事人的利益,因为,这些当事人在较早时期就是大律师的选举人,到后来才成为他的付款人的,但是,一个法学专家走向成功之路要依靠他的公会的好评;显然,在我所描写的这样一个制度下,要达到这样一个结果,就必须把每一个案件作为一条重大原则的一个例证或是一条广泛规定的一个示范来考虑,而不能斤斤于个别案件的得失。另外一种更有力的影响,发生在对各种可能的问题任意提出或创造,不加任何明确的限制。资料既然可以任意增加,则发展成为一条总则的方便便也无限地增多。法律是在我们自己中间执行的,法官不能逾越展示于他或他的先辈之前的各种事实的范围。因此,受到审判的每一种情况,借用一个法国成语,就被奉之为神圣。它具有与每一个其他真正的或假设的案件不同的某种特点。但是在罗马,像我已经在前面企图说明的,没有像“法院”或“审判院”这一类的机构;因此,也没有一组事实会比其他事实具有更多的特殊价值。当有一种困难提交法学专家征求意见时,决没有东西会阻止一个赋有很好类比力的人立即进而援引和考虑同它有些联系的全部假设问题。不论给予当事人的实际劝告是怎样,其由倾听着的学生在笔记簿上慎重保存起来的解答,无疑地会考虑到由一重大原则所能适用的、或为一条包罗无遗的规定所能包括的一切情况,在我们中间,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并且应该承认,在对英国法提出的许多批评中,它提出时所用的方式似乎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的法院所以不愿直截了当地宣布原则,很可能不是由于我们法官的禀性,而是由于我们的先例比较少,虽然我们的先例,在不知其他制度的人看来已是卷帙浩繁的了。就法律原则的财富而论,我们显然比有些现代欧洲国家贫乏得多。但必须记着,它们是以罗马法律学为其民事制度的基础的。它们把罗马法的碎石残屑建筑在它们墙垣之中;但就其材料和工作技巧来看,则并没有使它好过英国司法机关所造的建筑物。
罗马共和时期是使罗马法律学具有特别性质的一个时期;在其最初的一部分时间中,法律的发展主要依靠着法学专家的“解答”。但当它临到共和国衰败的时候,在“解答”的形式上,显示出它们已不可能再作进一步扩展的预兆。它们已经开始系统化,并且被提炼成为纲要。据说,曾有一个名为缪子·沙沃拉(Q. Mucius Scevola)的“教长”(Pontieex)公布过一本包括全部“市民法”的手册,在西塞罗的著作中,也显示出对于旧方法日益不满的迹象,所谓旧方法是指与法律改革这26 Franc.She
220330671.doc
个更活泼的手段比较而言的。到了这个时候,其他各种媒介也在事实上对法律开始发生影响。所谓“告令”(Edict)或“裁判官”的年度布告已被日益重视,并用作法律改革的主要手段,而哥尼流·西拉(L. Cornelius Sylla)把称为“哥尼流律”(Leges Cornelie)的大量条例经过立法而制定为法律,就显示出用直接立法的方法能达到如何迅速的改进。至于对“解答”的致命打击则来自奥古斯多(Augustus),他限制少数主要的法学专家对案件发表有拘束力的意见的权利,这个变化虽使我们能更接近于现代世界的观念,但显然根本地改变了法律职业的特点以及它对罗马法影响的性质。在一个较后的时期中,另外一个学派的法学专家又产生了,这些都是各时代中法律学的巨大人物。但是阿尔比安(Ulpian)和保罗斯(Paulus)、该雅士和巴平尼安(papinian)都不是“解答”的作者。他们的作品都是论述法律特定部门尤其是“裁判官告令”的正式论文。
罗马人的“衡平法”以及使衡平法成为其制度一部分的“裁判官告令”,将在下面的一章中加以研究。至于对“制定法”,须要说明的只是它在共和时期是很少的,但到了帝国时期则有大量增加。在一个国家还是青年和幼年的时代,绝少要求借助于立法机关的活动以求对私法作一般的改进的。人民所要求的不是变更法律,这些法律通常被估计得高过它们的真正价值,人民的要求只在能很纯洁地、完善地和容易地执行法律;一般是在要除去某种大积弊,或是要处理阶级与阶级之间和朝代与朝代之间某种无可调和的争执时,才求助于立法机关。依罗马人看来,在社会发生了一次重大民变后,必须制定一大批的条例,才得以安定社会秩序。西拉用“哥尼流律”来宣布他的改造共和国;朱理亚·凯撒(Julius Cesar)在“制定法”中作了大量增加;奥古斯多促使通过了最重要的“朱理亚律”(Leges Julie);在以后的一些皇帝中,最积极于颁布宪令的是像君士坦丁(Constantine)那些要想统治世界事务的君主。真正的罗马制定法时期要直到帝国建立以后方才开始。皇帝们的各种立法起初还伪装经过群众同意,但在后来就毫不掩饰地利用皇权,从奥古斯多政权巩固后到“查斯丁尼安法典”(Code of Justinian)公布,这种法规有大量的增加。可以看到,甚至在第二个皇帝的统治时期内,法律的条件和其执行的方式就已逐渐地接近于我们都熟悉的了。一个制定法和一个有限制的释义局已产生了;一个永久的上诉法院和一个特许的评释集将在不久之后产生了;这样,我们就被带到更接近于我们今日的观念了。
Franc.She 27
